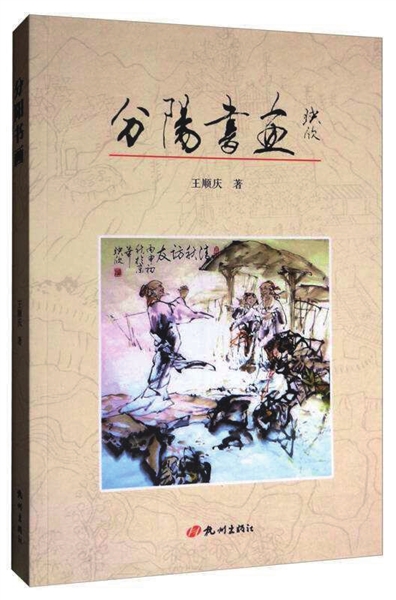| 穿行在分水儒学的殿堂里 |
| http://www.tlnews.com.cn/2019年11月23日 09:40:33 |
| ——王顺庆《分阳书画》赏析
■陆春祥 2016年2月8日,丙申年正月初一,上午十点,日光暴烈,真的是寒冬里的烈日,这一天的气象预报说,二十八度以上。 我和毛夏云、陆地一起,白日里去探春。 从白水村出发,往西南方向的冯家徒步。过银盘山,满山层次感极强的绿地毯,那是茶叶,虽无“春山半是茶”,但茶叶在暖温下已经发春,无疑。到了铜桥湾,一潭碧水湾绕,驻足良久,走吊桥,观民宿,打石漂。过栈道山,并无栈道,只有危岩乱石,竹林茂森,杂树生花。又过广丰庵,自然,也没有庵了,我们小时候叫白夜庵(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,大人们都这么叫)。跨过罗佛溪,对面是赵家村,不是鲁迅小说里那个有名的赵家,那是在绍兴。 两个多小时,走走停停,绕了一大圈,带着一身汗水,到达广王岭,白水村对面。抬望白水,村后就是白水坞,山势递次推进,层峦叠嶂,烟树如水浩淼,颇似陆坚先生的山居图景。坞的最顶处,有白水尖,我和陆地说,那里,最高峰,有个飞机目标,我们少年时砍柴,常到那去,有时望得见天上的飞机,一去一回,要一整天,背着一根百多斤的实木柴,疲倦回家。 诸位,刚刚我徒步的路线,是沿着清光绪三十一年修订,次年刊行(1906年)的《分水县地图》所标记的地名行进的。我所在的村,属于分水县的西乡,地理上都叫四管,范围极大,有好几个乡。四管的南和东,叫五管,和淳安、建德交界;四管的北和西,叫八管、九管。一百一十年后,人是物非,地名很多只存在于历史和人们的方言中了。 这张地图,就是王顺庆先生的新著,《分阳书画》第一卷里的一张普通地形图,繁体字,粗线条,山峦河流,村郭人家,似乎都跃然于发黄的宣纸上。 有人问我,如果穿越历史,最喜欢历史上的哪个朝代?我说最喜欢宋朝。好,现在,我仍要沿着这本书里的《南宋淳熙分水县地图》,去分水县儒学读书了。 这回,我坐船。 我家门口就可以坐船,就如同屈夫子“朝发轫于天津兮,夕余至乎西极”样方便。往罗佛溪(也叫百江),走两百米不到,就是溪口。对面的广王庙,香火常年旺盛,香客来来往往,买舟行船,晨行暮达。 一路行得船来,两岸青山相对出,时而猿猴悲鸣,时面空山鸟飞,几十里水路,由罗佛溪转入天目溪,河面宽阔,水流平缓,往来船只频梭,不一会,就到了县城的桥口渡。 这里就是繁华的分水县城啊! 过朝京坊、阜民坊,阜民坊边有塔,七层,仰望,塔身坚实,檐飞铃脆,塔院里不时传来阵阵诵经声。经庆云寺,到庆云坊,就到达分水县的地标玉华楼了,这是南宋分水最豪华的酒楼,史载,孝宗帝曾御此楼。王顺庆在他的《汾阳诗稿选赏》一书里,引了宋人黄铢的词《江城子·晚泊分水》,来形容南宋分水的繁荣,有词为证:“秋风袅袅夕阳红。晚烟浓,著云重,万叠青山,山外叫孤鸿。独上高楼三百尺,凭玉楯,睇层空。人间日月去匆匆。碧梧桐,又西风。北去南来,销尽几英雄。掷下玉尊天外去,多少事,不言中。”此词如闲适风情画,逸笔虽草草,却尽状其妙处,高楼观世井,风景别样情。 我也是在一个秋后的傍晚到达分水的。我乃穷书生,靠着父亲微薄的薪金读书,没有多少闲心,欣赏酒楼的繁华,朱门酒肉香,三百尺高呢,不敢进去,我要去县学苦读,我的目标是,一百里地外的南宋都城临安,那里有中国最好的太学,那里有我日夜向往的锦衣玉食!不要笑我狭隘,大多数南宋的同学,都怀抱这样的理想。 终于到达县学。 现在,我要向你绍介一下我的读书环境了(参《康熙分水县志儒学图》)。 我们的学校,在县政府的正对面。整座分水城里,最显眼的建筑,就是县衙、儒学、书院、城隍庙和钟楼了。 学校有教谕衙,教育局长办公的地方,全分水县教育的首脑指挥中心,明伦堂,文庙,大成殿,这些学校的主要建筑,我们要在那里读书学习。我们住的馆舍,宽敞明亮,从一号楼到四号楼,每一座馆舍,都很精致,政府在教育方面肯投资。我们每天的任务,就是读书明理,交流讨论,节日祭典孔圣人。局长教育我们,将来要成为国家的栋梁,将金人赶回北方去,统一祖国,发愤读书。 我们的学校,也是名人辈出(参第二编《进士图像》)。 我校先前那些名人就不一一细说了,唐朝的进士施肩吾、徐凝、缪迁,那真是太有名了,他们是母校永远的荣光。 42位进士,一百多位举人,数百位贡生。就如宋代,我们学校就出了17位进士,最牛逼的王家,教育如此成功,一门就有16位进士。 我们的图书馆,藏书量丰富,不仅有丰富的经史子集,更有各类家谱和校友们的经年妙品(参第三编《宗谱图绘》、第四编《名家字画》、第五编《乡人书画》),许多作品,匠意高远,笔墨清润,元气淋漓,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,我们常常观赏临摹,学业大进。我们感知前辈锥骨刺股的苦学,我们体悟前辈卓越的艺术成就,我们被家族的整体荣誉感所激励,我们也将努力创造辉煌! 当然,还有一些大家,也经常会光临我们学校指导。 举一个名人的例子,文徵明也来过我们学校。文先生,为什么来学校,有哪些人接待,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,他为“天尊观”题写了额扁。我想,这位先生,应该是在早春的二月,应某位文友之邀,说不定是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的,踏进分水的土地,清泥已萌兰芽,东风吹来温度适宜的煦风,也有细雨微斜,心情大佳,欣然题词。看看,他的字,骨气兼沉稳,散朗而多姿。 诸位,请不要笑我逻辑混乱,一会儿现实,一会儿穿越,这其实是我读王顺庆《分阳书画》的真实感受。王顺庆先生,沉浸在分水的历史里已多年,敝裘羸马,长途跋涉,上下一千三百多年的人和事,大略已参差胸中矣。他在替我们分水的千年历史着急,劳思焦心,我从内心尊敬他。 你也不妨深入书中,翻阅浏览,那么,分水的千年历史,一定会在你脑中,和你的现实,交错相映。 1980年7月,分水中学文科复习班参加高考,有16位同学考上了本科和专科,一时全县轰动。我们读书的分水中学,就是今天的五云山,南宋的庆云书院。 人事虽已替,千载有余脉。此脉,即传承至今的分水悠久历史文化。王顺庆先生,是其中的一分子,也是热心接脉人。尔后,分水文脉,仍将不绝而绵延! 是为序。 (本文为《分阳书画》的序言) |
| 原标题: 穿行在分水儒学的殿堂里 |
| 作者: 网络编辑:周叶剑 |